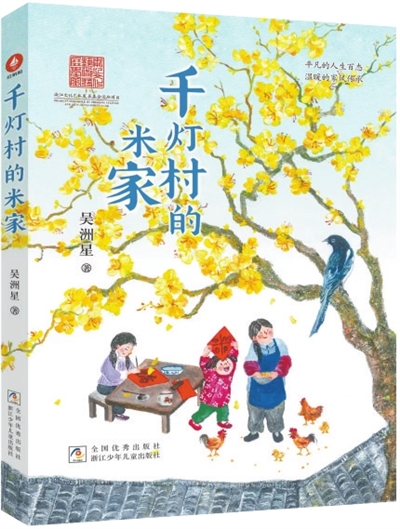○叶一格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千灯村的米家》深度继承并创新发扬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吴洲星将目光精准地投向凡俗烟火,让故事围绕米桃一家的喜乐悲欢徐徐展开,凝聚起人世间最朴素真挚的情感以及关于团圆的美好期许,以文学独有的温情方式为小读者们传递善与美的滋养。
小说开篇仿若一曲田园牧歌,年少不识愁滋味的米桃心里,唯有一个“盼”字,盼大雪盼过年。千灯村劳作一年的人们在这个特殊节点抛下俗务,尽情沉浸在生活的喜悦中,让人想起遥远的《诗经》所写“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那种劳作后的惬意与松弛,作者还巧妙融入了墨笔红纸书写的送福、拼蛋习俗等诸多具有千灯村特色的细节,赋予整个故事陌生化的乐趣与生活化的质感。
佩里·诺德曼说:“儿童文学的语言应该是透明的”。《千灯村的米家》深度契合这一理念,在扫除儿童阅读障碍的同时,完好地保留了文学性,这得益于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对叙事的高度节制。作者对小说语言也进行了精心打磨与反复锤炼,使其达到一种简洁直白却又引而不发、饱含张力的绝妙境界,充分结合儿童与生俱来的感知力,故事里有拼命想要证明自我的雪花、乖巧坐着的稻秧、随心撒欢的风、顽皮挑衅的麻雀……一切景致都生机盎然,洋溢着童真意趣,呈现出明亮活泼的小说基调,农忙时节也颇有陶渊明笔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自在气韵,极力渲染出让人无限向往与眷念的理想田园氛围。
小说采用线性叙事,结构精巧,情节流畅自然却不失起伏。买鞋、看病、家访、卖米、稻客到来等等看似独立又紧密连接的事件,像是结在藤蔓上的一串甜美诱人的紫葡萄,不断激起读者寻求答案的强烈兴趣。作者对文学意象的选取精妙独到,例如,“福”的笔画、米桃爸爸种下的黄腊梅的五朵花瓣,皆与米家五口人相呼应;而团圆夜的饭桌上由碗盘拼成的“花朵”,漫溢着人间烟火味。结尾处再次出现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元素——在米仓里紧紧相依的五个粉笔小人和米桃心里得而复失的“福”,似乎把一切又带回到米桃期盼着的故事开端。这种宿命般的回响,蕴含着作者对情感层次的细腻把握和成长主题的深刻思考,也让读者在经历漫长的跋涉后,终于与米桃一起抵达饱含希望的黎明时刻。
《千灯村的米家》的群像化塑造有着令人惊喜的分寸感,举重若轻、繁简得当。书中人物并未被所谓的主角光环所遮蔽,而是在作者笔下逐渐长出了自我的血肉与灵魂:庆胜利满怀热忱、天性纯真,却拙于言辞表达;春妹为人直爽、重情重义,然行事风格稍显跳脱;李老师外冷内热,脾性之中带着几分火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儿童文学是启蒙时代诞生且延续的火光,如何处理沉重感是儿童文学创作走向内化、深化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吴洲星从不回避那些必然的分离、死亡的隐喻与生活的艰辛,而是站稳了以善为美的根基,将个体成长路途上的锐利阵痛化作柔软且充满想象力的瞬间,用明亮的色调中和生活的黯淡,轻盈完成了现实人生的诗化。《千灯村的米家》的现实书写并不是对主题性写作亦步亦趋地跟随,而是扎根真实人生并共情世间万象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为小说赋予了温暖的治愈感。
吴洲星极为可贵的共情能力和对生活细腻入微的描摹能力在《千灯村的米家》的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秉持对人物主体性的尊重并深入挖掘角色内心,拒绝构建乌托邦式的田园世界,而是以悲悯之心拥抱了这个急剧前进着的时代,从城乡的碰撞间找寻思考的火光。尤为关键的是,她通过笔下人物的成长,让更多的小读者相信,在善意的滋养下,我们可以拥有达观勇敢面对世界的能力,与所有的不完美和解。
(作者单位:鲁迅文学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