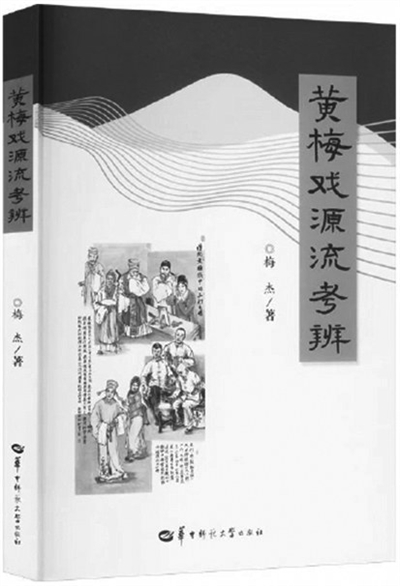○黄羊山
小时候本村及周边村庄经常搭台唱黄梅戏,至于唱的什么并不感兴趣,高兴的是图个热闹。及至工作后,时常关注关于黄梅戏的起源及传承问题。在看到更多的资料后,逐渐认识到黄梅戏的成戏应该与传说在黄梅县得道成仙的宋益有关。
宋益为东晋时福建人,曾任番禺县令、睦州刺史,因不愿做刘宋之官,便拂睦州刺史,挂印而去。此后遍游名山大川,至黄梅县考田山(黄梅山),得一福地,遂在此修炼成仙,历代多有封号,民间习惯称昭德侯(王)、福主菩萨,留有众多古迹和故事传说,尤其是每年都有隆重的祭祀活动。在明清时期的府志、县志里以及一些人的诗句中,都有二十七村轮流接应福主菩萨,建坛设额祭祀,并搭台唱戏酬谢。笔者所在的村庄旧属长安村,为二十七村之一。更有甚者,笔者曾经调查过濯港镇胡牌村(旧属二十七村之网埠村),有一年唱戏要从大年初二唱到清明节,中间还要换戏班子。
2024年,梅杰关于黄梅戏起源的文章频出。尤其是借助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梅杰搜集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梅杰每有新作出来,我必认真拜读,并与其互动,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初,梅杰将其近年文章结集出版,即《黄梅戏源流考辨》。随后在梅杰《黄梅戏源流考辨》的基础上,特地翻看了明弘治《黄州府志》、清康熙《黄州府志》、清顺治《黄梅县志》(在明万历《黄梅县志》残本基础上增编)、清乾隆《黄梅县志》、清光绪《黄梅县志》等,尤其是看了明代嘉兴知府徐霖、黄梅县令曾维伦和黄梅学者瞿九思的相关作品后,确信黄梅戏成戏与祭祀宋益密切相关。
今将几点思考写出,以供进一步探究:
黄梅戏因祭祀昭德侯(王)宋益而由村野畈腔登上戏曲舞台。明弘治时徐霖说,秋天收成之后理应先报祀昭德侯;万历县令曾维伦说十月为乡戏,是为了报昭德侯;万历时瞿九思说这戏是艳曲淫词不忍闻、看戏叫人易动心。他们相隔时间不远,可以相互印证。
黄梅戏中的许多人与事是黄梅县本土的,尤其於老四、张德和、胡彦昌、柳凤英、瞿学富等都是前述的二十七村人,说明当时登上戏台的不是外来的戏曲,而是本土的。
黄梅戏成戏的年代不迟于明万历年间,与昆曲的成戏时间大体一致,当时仅称其为戏、乡戏、香戏。过去认为黄梅戏形成在清康乾时期恐怕要往前推了。特别要注意的是明万历时,黄梅人石昆玉做过苏州知府,与瞿九思一样与汤显祖关系甚密,石昆玉、瞿九思、汤显祖、黄梅戏、昆曲之间有没有关联,值得深究。从《黄梅戏源流考辨》中可以看到,在晚清及民国时期,黄梅戏在安徽和上海等地饱受打压,但仍顽强生长,也许正是这段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黄梅戏在上海大放异彩打下了很好的观众基础。
从《黄梅戏源流考辨》中还可以看到,采茶戏的叫法出现于清康熙晚期及乾隆时期,更多的是在乾隆时期,但之前这个戏已经存在百余年了,只是把这一时期的戏叫作采茶戏,如果在黄梅县之外叫则加上地名,称黄梅采茶戏。称为黄梅戏则出现在晚晴,大概是黄梅采茶戏的简称,也比较上口(总不能别的称京剧、豫剧、越剧、评剧,这个还叫黄梅采茶戏吧)。书中资料还显示,在江西省多称其为黄梅采茶戏,在安徽省、上海市则多称其为黄梅戏、黄梅调,说明这戏是先向南传播,再向东传播。总结来说,在明弘治到清康熙晚期,称其为戏、剧、乡戏、香戏(好比人的小名、乳名);在康熙晚期到晚晴,称其为采茶戏、黄梅采茶戏(好比人的大名);晚晴之后,称其为黄梅戏。
黄梅戏向外传播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社会分工的过程中,基于祭祀神灵并唱戏的需要,形成了专门的戏剧班社,唱戏是他们的优势。当黄梅县周边也开展这一习俗时,会请已经比较成形的戏班去唱戏。在其他时间这些戏班也会寻求去外地的演出机会以挣钱谋生,再往后演戏之处慢慢地也有人跟着学唱戏谋生。这大概是黄梅戏传播的主要途径,还需深入研究。
总之,《黄梅戏源流考辨》必将开拓人们的视野,产生新的思路,把黄梅戏的溯源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