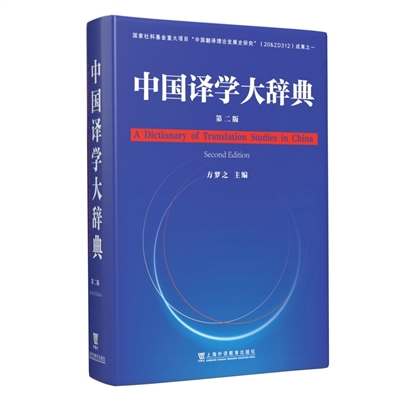■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管若潼
《中国译学大辞典》作为系统整合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性辞典,被誉为“翻译学的百科全书”。近日,《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初版到第二版的编纂历经了20个春秋,系统收录译学术语近2600条,划分为26个学科大类,全面覆盖传统译论、本土学派及人工智能翻译等前沿领域。其修订历程不仅是一部学科工具书的升级史,更折射出中国学术界从文化觉醒到理论自信的变化。方梦之作为《中国译学大辞典》的主编,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当代译学在继承传统译论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国外译学优秀成果并不断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该书主编、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方梦之教授,探寻辞典背后的学术传承与时代创新。
从“学徒期”走向“自主期”
《中国译学大辞典》初版于2011年面世,而其筹备阶段早在本世纪初便已开启,初版的《中国译学大辞典》记载着中国译学的“学徒期”阵痛。“那时,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刚刚确立,译学话语体系尚在酝酿之中。”谈及2011年《中国译学大辞典》首版编纂的背景,方梦之说道。20世纪末期,国外翻译研究转向频仍,西方范式更迭让学者们应接不暇,中国译学界经历着震荡期,充斥着西方话语的高调嚣呼。“面对纷繁复杂的范式更迭和交替,国内学者们忙不迭地引进套用,急于借助新的方法和视角,往往还未来得及做好前一种范式的理论准备,下一个‘转向’接踵而至。”
这种状况在新旧世纪之交迎来转折。随着我国译学完成了“与国际接轨”,进入了自主研究的独立学科阶段,大规模引进告终。方梦之指出,这一时期,国外译学资源锐减,我国译学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引进为表征,而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范畴的拓展和自创话语体系为特征。国内学者开始重视传统译论,汲取我国传统学术之精华,挖掘传统译学术语,以此作为建构我国译学话语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译学展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和原创性,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中学与西学并驾齐驱,新理与旧学各行其是。
初版《中国译学大辞典》从相邻学科引入概念,吸纳了来自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信息论、认知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术语,为创新译学话语表达方式铺路,为翻译学的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然而,初版素材基本出自上个世纪,有些词条出版时已显滞后,不少词条该收未收。
同时,随着我国翻译专业的崛起和翻译市场的发育,培养翻译人才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日益重要。2006年,翻译专业在我国本科招生名录中已赫然在目;2007年,翻译专业硕士开始招生。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加强,创新理论不断涌现,这些都促使《中国译学大辞典》的修订工作提上日程。“为了反映我国译界新世纪以来的自主创新成果,彰显我国学者的本土理论,借鉴国外译学新论,弥补初版的不足,促进我国译学的发展,我们启动了初版的修订工作。”方梦之补充道。
推陈出新,2600个词条搭建学科框架
为了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译界的自主创新成果,弥补初版的不足,促进译学发展,方梦之带领团队启动了《中国译学大辞典》的修订。方梦之表示,第二版《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大部分新增词条反映了国内外近20年的研究成果,提炼了一批新范畴、新概念、新术语,充分反映了我国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特别选收了6种影响广泛、新世纪涌现的翻译理论,如变译论、生态翻译学、应用翻译研究、文章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国家翻译学。此外,第二版在借鉴国外,吸收国际译学研究的新术语的同时,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力求反映我国译学研究的传统脉络和当下水平,做到科学化、精细化。“我国前期翻译研究的‘接轨’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立足本土,创新理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方梦之说道。这种文化自觉,贯穿了《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编纂过程。
具体来看,第二版对初版词条润改逾半,重写了部分词条,删减了少数过时的词条,并新增700余条词条,词条总数从原1900条增至约2600条。方梦之对于新增词条的编纂着重在五个方面:一是挖掘传统术语。第二版《辞典》挖掘了一批佛经翻译术语,例如,“味”“境”“化”“隔”“圆”“妙”“和”“真”“言”“修”等佛经翻译范畴词,系统收录摄摩腾、康僧会等著名佛经翻译家,同时增收了以鲁迅、傅雷、钱锺书等为代表的现代翻译概念,他们在当时的语境中充分表述了其译学思想,奠定了今日译论的话语基础。二是提炼当代概念。新概念伴随着新思想、新范畴的产生而产生,而创新的术语是表述新概念的有力工具。第二版新增了如“国家翻译实践”“阐释关键词” 等新范畴。三是引进外论。虽然大规模引进已成过去,但是吸收、借鉴西方理论,如“娱乐化改写(rewriting for entertainment)”“数字化翻译(digitalizing translation)”等,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四是完善已有表述。概念的表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与学科发展而不断完善。第二版更新了部分表述,充实了次级概念。五是补充翻译史实。长期以来,我国翻译史研究存在重文学,轻科学的倾向。翻译史研究如果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挖掘并弘扬对我国近现代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重要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为此,第二版收入了一批对学科的引进和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专家兼翻译家,如以社会学闻名的费孝通、以语言学闻名的高名凯、以哲学闻名的贺麟等。
此外,《中国译学大辞典》将译学术语分为26个大类,翻译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是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甚至超学科研究,与文理各科都有着盘根错节、牵丝攀藤的关系。为了便于“按图索骥”,又能符合学科逻辑。第二版《中国译学大辞典》以“一体三环”的译学发展时空图为结构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知识体系。“一体”即译学本体,是译学发展之本;“一环”是语言和语言学等译学发展的原初性、奠基性学科;“二环”是译学发展的支持性、工具性学科;“三环”是文化与技术,将文化与当代科学技术相联系,使翻译研究具有数字化特征。同时,还包括“翻译教学”和翻译史类目,构建了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知识体系。
当翻译遇见人工智能:危机还是新生?
在第二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编纂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方梦之表示,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找到合适的人撰写合适的词条。“翻译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要找到在某一话题上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积累的作者并非易事。”他举例说,“比如翻译技术近几年发展很快,但是这方面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的作者在国内比较少,寻找作者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个人学术网络。”方梦之几经周转找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华树教授,而在这本辞典中积累下来的作者资源也为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参考。
如今,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迅猛发展,AI翻译迅速占领市场。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对于翻译理论的冲击时,方梦之认为,从译学研究的角度看,二者并非矛盾关系。传统译论要传承,人工智能要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译论的研究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有应用的空间,比如翻译标准可以对翻译进行指导。同时,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也将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路径产生影响,会激发新的翻译理论探讨。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工智能翻译是翻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方向。方梦之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词典编纂出版周期长,人工智能迭代更新快,词典总是落后一些,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他坚信,在《中国译学大辞典》(第二版)出版后,还会有新的相关学术成果不断问世,虽然形式会发生变化,但我国译学研究和译学建设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