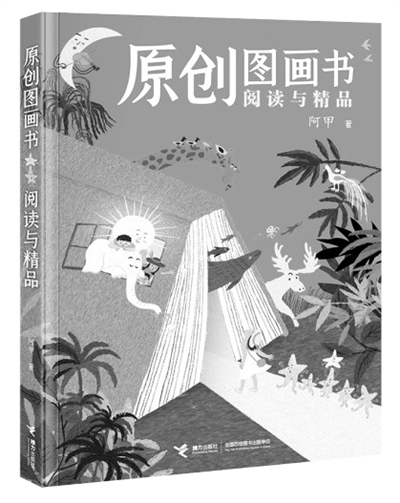■受访人:阿 甲(童书研究者、童书作者、译者)
□采访人:孙 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近日,阿甲的《原创图画书阅读与精品》在接力出版社出版,他的讲述如同一部流动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史。从《萝卜回来了》的质朴到《绿洲》的先锋,从“如何交朋友”的童年困惑到“物种灭绝”的人类困境,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变迁,更在构建一个共情的世界。正如阿甲所言:“我们不是在创作图画书,而是在创造连接的可能。”在这个AI与全球化交织的时代,这种连接,或许正是人类最珍贵的护城河。
成书的渊源
□您策划《原创图画书阅读与精品》的契机是什么?
■这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5年。这些年我翻译了300多本图画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梳理中国本土创作的难度远超预期。国内早期资料零散,创作者访谈耗时长且动态变化——比如蔡皋老师的《宝儿》1993年获奖后多次调整版本,彭懿老师的作品也在持续迭代。直到2021年白冰老师邀请我编写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梳理的机会。
□这套书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筛选标准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历史价值,如《萝卜回来了》(1955)最初虽排版简疏,但插画的现代性远超时代;二是创新性,像《企鹅冰书》用变温材料呼应冰川主题,可惜因版权问题未能收录;三是国际共鸣,如《安的种子》同时斩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和美国弗里曼图书奖,证明东方哲学的普世性。
□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历程有哪些关键节点?
■2000年是真正的分水岭。此前作品多为连环画或儿童图画故事书,如《萝卜回来了》最初采用骑马钉装订,文图叙事在方向上比较随意,但插画色彩至今仍显时尚。2000年后,我国台湾地区的《妈妈,买绿豆!》《子儿,吐吐》《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我有友情要出租》等作品传入大陆,启发了本土创作。2008年是爆发“元年”。《安的种子》《团圆》《一园青菜成了精》集中问世。这并非偶然——市场接受度提升、创作者技法成熟(如熊亮的“野孩子系列”)、编辑团队(如海燕出版社郑颖团队的“棒棒仔”系列)的推动,共同促成了这场“井喷”。
聊聊入选作品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选得很少,但选了《宝儿》?
■《宝儿》原名《荒园狐精》,由蔡皋创作于1991年,1993年成为中国首部斩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的作品,堪称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中国图画书多以连环画为主,《宝儿》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图画书开本与叙事结构,证明本土创作者完全有能力与世界对话。尽管后续版本调整了文字排版,但核心插画仍保留了原始张力。这个故事改编自聊斋故事,讲述一个商人的孩子宝儿斗智斗勇斩杀狐妖的故事。蔡皋的插画在民间色彩的大胆运用上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团圆》也是国内原创中不得不提的存在。
■余丽琼文、朱成梁图的《团圆》是2008年爆发期的代表作。故事以春节为背景,通过父亲回家、离别时留下一枚硬币的细节,展现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朱成梁用暖色调水彩描绘江南水乡,硬币的“团圆”象征贯穿始终——硬币被孩子藏在棉袄里,最终成为“好运硬币”,暗喻亲情虽短暂却永恒。这本书可以说引发了“流动中国”的集体记忆,获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首奖,并入选2011 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插图童书。其成功在于将宏大的社会议题转化为可触摸的童年体验。
□《安的种子》为何能成为现象级作品?
■这本书的成功是文、图、编辑三方打磨的结果。王早早的文字本是一则家庭教育寓言,但黄丽老师通过采风寺庙生活,将“等待与正念”的哲学具象化为图像语言:前环衬的积雪与后环衬的莲花呼应,人物服饰的素色暗含修行者的克制。美国弗里曼图书奖评委的解读更值得玩味: “这是一个关于正念的温和寓言。”这种多义性恰恰是图画书的魅力——孩子看到故事,成人看到隐喻,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找到共鸣点。
□您为何选择《我有友情要出租》作为经典案例?
■这本书销量预计超300万册,是早期校园推广教科书级的案例。作者方素珍与画家郝洛玟是好友,绘者的深度参与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原来的故事,这在图画书创作中并不多见,图文作者默契十足。这种默契让文字与图画产生了“错位叙事”的美感:大猩猩始终未发现身边的小老鼠,而读者却能通过画面捕捉到友情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一个时代痛点——2000年代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编辑团队联合《中国少年报》开展“知心姐姐”调查,将共读场景延伸至课堂,最终让这本书成为教师培训的“教具”。这种“内容+推广”的闭环模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完整版请见编客实验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