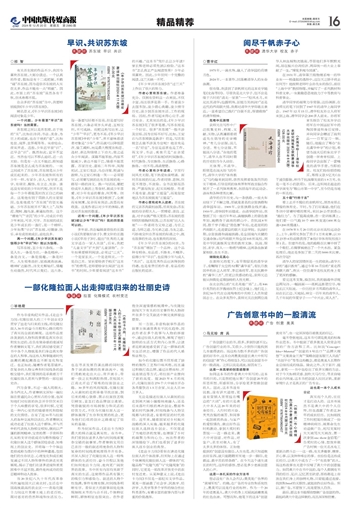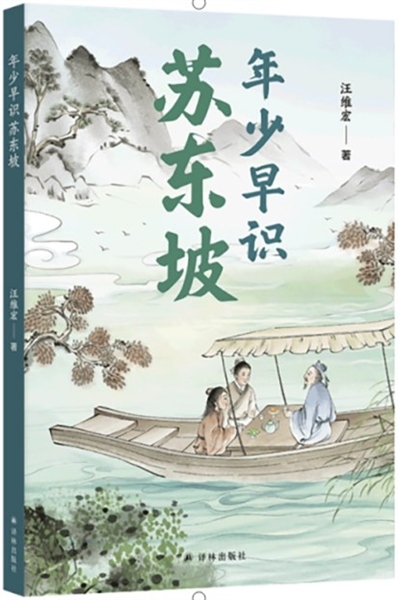○祁 智
有关苏东坡的作品不少,我因为喜欢苏东坡,大部分读过。一个认真的作者,假如没有十二成把握,不敢“碰”苏东坡,因为追崇苏东坡的人实在太多,作品不能有一点“瑕疵”。因此,市面上的“苏东坡”虽然各有千秋,但水准都不低。
在众多的“苏东坡”当中,我要特别提到《年少早识苏东坡》。
顾名思义,《年少早识苏东坡》的阅读对象是少年。
一个问题。少年需要“早识”苏东坡吗?当然需要。
苏东坡之所以是苏东坡,在于他的“实”,比如在诗词、书法、美食、为官上的成就,也在于他的“虚”,比如处世、境界、世界观等等。实虚结合,虚实并进。这些,少年迟早要“识”、迟早会“识”。既然如此,宜早不宜迟。当然也可以不那么迫切,迟一点无妨。但是有一点又不能迟,即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成为苏东坡的。一夜之间成不了苏东坡,苏东坡是从少年成长起来的。少年苏东坡和所有的少年一样,有家乡、亲人,有学堂、求学,有顽劣、醒悟,有立志、发奋。谁还没有顽皮的少年时代呢,但并不是每一个少年都能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是他有别于同龄人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成为“苏东坡”的坚实基础。少年苏东坡并不“高大上”,玩和泥、爬树、掏鸟蛋,普通如你我。这个“接地气”“亲民”的少年,对成长中的少年来说,可亲、可学。苏东坡的成长是少年成长的一盏灯,是一个榜样。少年如果“早识”苏东坡,对健康、快乐、卓有成效地成长,益处良多。
再一个问题。《年少早识苏东坡》值得少年“早识”吗?我以为值得。
写苏东坡,至少有六条线。一条是人生,一条是为官,一条是精神,一条是诗文,一条是情趣,一条是时代。人生艰难曲折,宦海波涛汹涌,精神旷达豁然,诗文光辉灿烂,情趣生动盎然,时代风云变幻。这六条,每一条要写好都不容易,但是要写好苏东坡,六条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交织,不可或缺。而把这些写出来,让“少年”“早识”,更为不易。《年少早识苏东坡》中的“少年”,并不意味着读者对象是“少年”,作品就可以降低层次、偷工减料,而是最大程度在构思、选材、表达和情绪上下功夫,使之适合少年阅读。谋篇不能笨拙,内容不能减少,表达不能干巴,情感不能直露。苏家历史、嘉祐二年科举、凤翔初试、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贬谪与救赎、与王安石相逢一笑……必须要写,必须要写到的还有苏东坡的走一路写一路的诗文。换一句话说,要把给成年人做的上等食材,做成少年喜爱、对少年有益的餐食,何其难。但是,《年少早识苏东坡》做到了,全面而有侧重,复杂而有简洁,泼墨而有收敛。这是作者以对少年的体贴,表达对苏东坡的敬重。
还有一个问题。《年少早识苏东坡》能让少年“早识”吗?我的回答是可以的。
多年前,我在编辑黄蓓佳的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时,提出“优秀的儿童文学适合一家人共读”,后来,我把“儿童文学”扩大到“儿童读物”。少年如果要顺利阅读,必须过“三关”,一个是家长关,一个是老师关,一个是自己关。家长要给孩子购买“这本书”的费用,老师要给学生阅读“这本书”的时间,少年要有阅读“这本书”的兴趣。“这本书”凭什么让少年读?家长和老师必须先读以检验。“这本书”怎么真正产生阅读效果?少年必须喜欢。因此,少年任何一个完整的阅读,这三关缺一不可。
《年少早识苏东坡》在“过三关”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作者心里有苏东坡。作者准备充分。仅拥有资料这一点来说,不仅丰富,而且很多是第一手。作者没少去图书馆,没少潜心典籍,没少搜寻历史,没少到苏东坡生活、工作的现场。因而,作者写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尤其突出的是,《年少早识苏东坡》花了很多笔墨,写苏东坡是一个好官。很多“苏东坡”一般不涉及官场,因为官场不好写,比如,王安石与苏东坡孰是孰非?但是,写苏东坡怎么能不涉及为官呢?他首先是一名“好官”,为官是追求也是工作,而文学、书法、美食只是“业余爱好”。《年少早识苏东坡》的时间脉络、时代脉络、为官脉络、生活脉络、心路脉络,一丝不苟,清清楚楚。
作者心里有少年读者。字里行间风光无限,笔下热爱如泉喷涌。面对苏东坡的厄运,作者同情、悲悯,但是不埋怨、不渲染。全书沉郁而昂扬、严谨而恢宏、纪实而畅想。作者不是有意、故意“正能量”,而是坚定地认为苏东坡就是“正能量”。
作者心里有成年人读者。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最初浪荡,后来发奋;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一贯博爱、善良、正直,对子女既严格又宽容;苏东坡的恩师欧阳修胸怀坦荡,让苏东坡“出人头地”……作者将为父母之道、为官之道、为师之道、为兄弟之道、为友之道,巧妙地交织在苏东坡的际遇之中,既有故事的生动,也有教育的深刻。
《年少早识苏东坡》的问世,为“苏东坡”增加了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有特色、有品质、不掺水、不糊弄,值得少年“早识”,也值得少年与成人“共识”。这是优秀作品应该得到的待遇,也是有责任的作者、有品质的出版社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