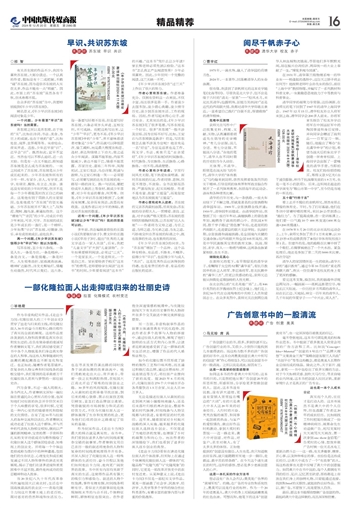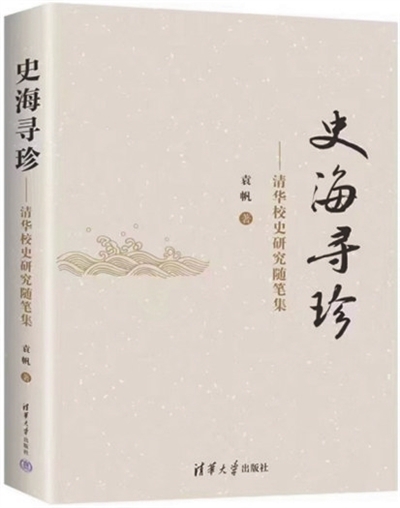○曹宇红
1975年,一滴水珠,融入了清华园的荷塘月色。
2024年,一本著作,回荡着清华人的生命浪潮。
很有缘,我读到了袁帆师兄的这本史学随笔《史海寻珍》。尽管我是北大学子,但不论是缘于古时的“清北一家亲”——“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还是近代的西南联大情,我都对清华大学仰慕且亲近,一直希望自己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危难中见激情
袁师兄在写作中广泛收集史料、档案、文献、实物,认真遵循着胡适先生倡导的史学精神,“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在他的笔下,清华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担当令人动容。
无体育、不清华。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清华大学的“体育教父”马约翰来到昆明,依然发挥着轰轰烈烈的实干精神,引导昆明的体育界和军政首脑合作展开了一系列体育教育,包括每年的运动会、游泳和各种球类比赛。
清华的百年历史,与一条铁路、一座火车站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就是著名的京张铁路和清华园车站。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开通;1910年,清华园车站建成。由清华园车站,我想到了另一座百年车站,滇越铁路上的碧色寨车站,她栖身于滇南的群山中。在抗战8年间,数千学子路过“碧色寨”车站,走进昆明的西南联大,走进蒙自的联大文法学院。抗战时期,京张铁路和滇越铁路,是全国境内关键的交通命脉;而西南联大和全国105所高校,则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教育文脉。抗战、报国、求学、育人……物质与精神,这两条血脉紧紧相依、生生不息。
细微处见真心
在袁师兄的笔下,有早期留美的清华学子,有翱翔于太空的52颗“清华星”,有抗日救国中的孙立人将军、李忍涛将军,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但更让我感动的是,袁师兄总能从细微处觅得独特的人性光辉。
在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上,有846位英烈的名字镌刻在烈士纪念墙上,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中共特工人员和爱国志士。在众多英烈中,袁师兄关注到两位清华人林良桐和沈镇南,尽管他们多年默默无闻,却在振兴台湾经济、两岸统一的大业上奉献了一生,“博览多阅为国谋”。
在1931年、清华第三级物理系唯一的毕业生——杨逢挺的选择中,这位天之骄子将去往何方?他按照老师叶企孙先生的指引,前往“上海中学”教授物理,并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和科普文章,一生勤勤恳恳地致力于中等教育与科普事业。
清华同学的凝聚力非常强,这份渊源,在袁师兄的笔下回到了1947年的清华上海同学会。1947年12月15日,清华校友孙立人将军来到上海,清华同学会200多人前来。孙将军首先报告了校友齐学启将军在中国远征军中的殉国事迹和身后安排,并向同学会赠送了战利品——日军宝刀一柄。随后,他提出了筹办“东北清华中学”的计划,希望为战火后的东北学子创建一所青青校园。上海同学会出版了一套精美的清华手册,当即拍卖。校友们纷纷捐资购买,筹得义款5亿元(由于通货膨胀,相当于抗战爆发前的1.9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后来,这所闻名遐迩的中学演变为“鞍山市第一中学”,至今仍是当地的一所名校。
五十载“行胜于言”
看上去并不健壮的袁帆师兄,居然有那么辉煌的体育史。平时,为了打好基础,他们在冬训中冒着呼啸的寒风,来回20公里到香山“跑拉力”。为了提高成绩,在一堂训练课上,他们要一口气跑10个400米变速(400米全速+200米慢速)。
在1978年5月20日的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上午,袁师兄参加了男子1万米竞赛,以33分23秒4的成绩获得了B组(非体育院校组)第1名。但意外的是,他的跑鞋在比赛中掉了一个鞋钉,右脚掌被磨出了一个大水泡。紧急处理后,他还是参加了第二天的5000米比赛,再次夺冠!
清华人的家国情怀是一生的底色;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通过今年10月份的“重走西南联大路”,我从一位位清华老校友的身上有了更深的感触。
看完这本文集,倏忽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两句诗、一幅画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位历经岁月风霜的清华人,站在长江边、天地间,神交一百年来的清华人、几千年间的华夏学子——“中兴业,须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