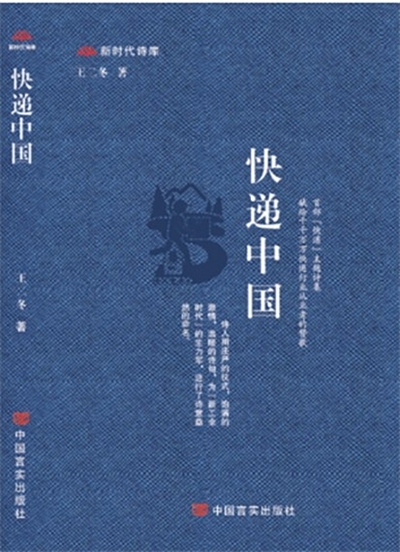○崔 博
王二冬以丰沛的创作热情和扎实的语言功底,以快递这一讲求精准、迅速,核心质素几乎与诗学相悖的行业为题材,拓耕出一片新的诗歌场域,并在这片场域中书写新时代的传奇。
在快递的场域中书写传奇,需要面对的诗学问题之一是:快递行业的特点,是精准、迅速、便利,但对诗学而言,这些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精准的意象组合,过于直白的修辞,会使诗歌语言失去活力和美感。诗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快递连接着当下的社会生活,但这“连接”是物理的、数据的,诗歌书写的难度在于,将其转化为诗学的“连接”。在诗集中,诗人穿透速度与精确度的表象,找到了“快递”与“万物”之间精神的连接:从塔什库尔干的高原草场到北极村的极夜白雪,从巴丹吉林沙漠到尼珠河大桥,诗人循着时代精神的脉络,以诗笔写宇宙、万物、众生。这样的诗学路径外化为诗集结构:奔跑者——分拣线——万物生。
只有超越物质的、数据的联系,才能建构出诗意的、情感的联系。这两种话语常常是相互排斥的,因此,诗人不得不在写作中不断化解矛盾。
总体而言,因为书写对象的现实性,诗人的诗歌话语是较为贴近生活的——诗集中使用了大量日常生活意象及口语化词汇。但日常并不等于平庸,诗人以平凡的人、事、物为材料,创造出包罗万象的万花筒。
“快递中国”的疆域有两个主体的支撑——包裹和送货员。在诗人对这两组意象的处理中,当代诗歌再次获得了处理驳杂现实的能力。
如果将王二冬诗中一个个笑中带泪的故事串联起来,会发现其内容几乎已经涵盖了我们全部的日常生活,甚至那些特殊的情景和时刻,如《冰山新来客》中,高山上的物流点;《雪花落满麦子屯》中,以当下乡村的温情,抚平历史的褶皱;《博物馆搬运记》中,与包裹惺惺相惜的快递员等。
“包裹”概念的延展、意义的深化,在拓宽诗歌表意疆域的同时,也呈示了诗人丰沛的想象力,如《单翅飞翔》中,“命运的恶作剧是一个无法拒收的/包裹”;《西行漫记》中赋予包裹生命。
有了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再加上巨大的同理心、开阔的胸怀与视域,才将这些以肉身的速度和意志的坚韧,连接着我们生活的快递员,书写得如此生动。诗人书写他们的饥饿(《河边野餐》)、疲惫(《任何一个家》)、低落(《播种者》)、困惑(《乡村使者》)。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体察到的,从不是单向度的负或正——他以强大的敏悟力,洞悉了生命及存在的深度和复杂性,表征在诗中,有离散中的相聚(《大雾中》)、低谷时的仰望(《星星》)、时光的逝去与代偿(《老王收快递的日子》)、肉身的脆弱与命运的强势(《我不知道风的方向》)、实象与倒影、形而下的收取与形而上的释然(《千年首单》)。
诗人面对的第二个创作难点在于,诗集的题材较难使用超出写实以外的创作方法。写实虽然保证了其诗歌抒情与叙事的及物性,但同时也束缚了其创作中语言创新的广度、诗歌技巧更新的向度。
诗人最大限度地拓宽了“快递中国”的丰富性:在同样的题材之下,书写爱和信任、时间与空间、铭记与遗忘、生与死的距离、宇宙万物、芸芸众生。诗人以细致的观察为传奇填充血肉(《城市超人》),连接生活与生命(《故乡的月》),言说众生之悲喜(《春海》)。
王二冬在诗歌中走遍了世界,却也从未离开过东河西营。因为这里,是他诗歌想象的现实支点。这个反复出现的地名,实则是承载了诗人丰厚记忆与丰沛情感的场域。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指出了认识内心空间确定位置的重要性。诗人在睡梦中,在白日梦中,在梦想中,不停地返回东河西营,才在高强度的工作下展现了旺盛的创作力,在生存的悬崖上窥见诗意,在时间的缝隙中挖掘生命能量,在新的场域中写下新时代的传奇。